|
晚清碑派名书家陶浚宣
洪忠良
此文载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杂志2009年第2期总233期第49-55页并封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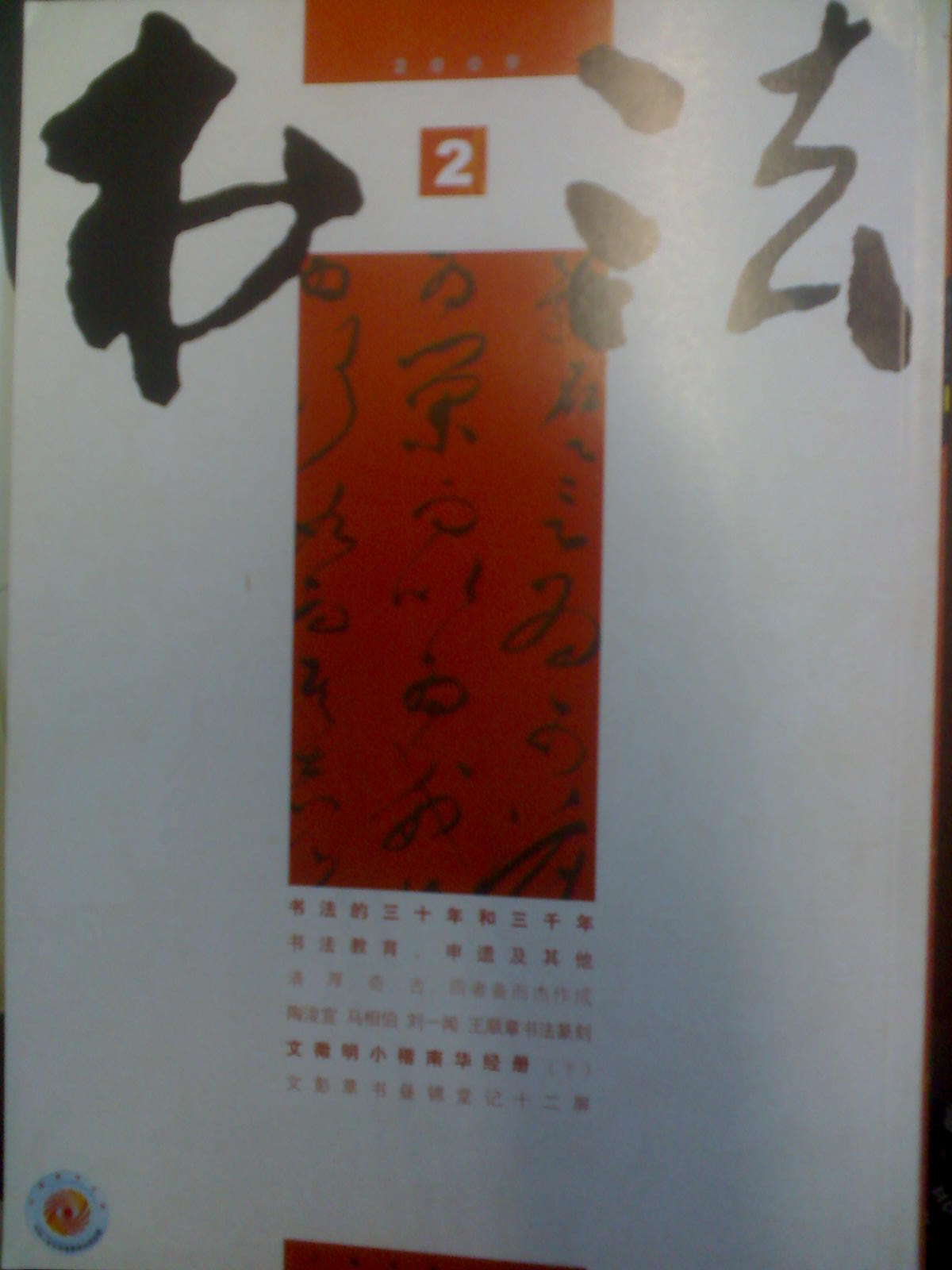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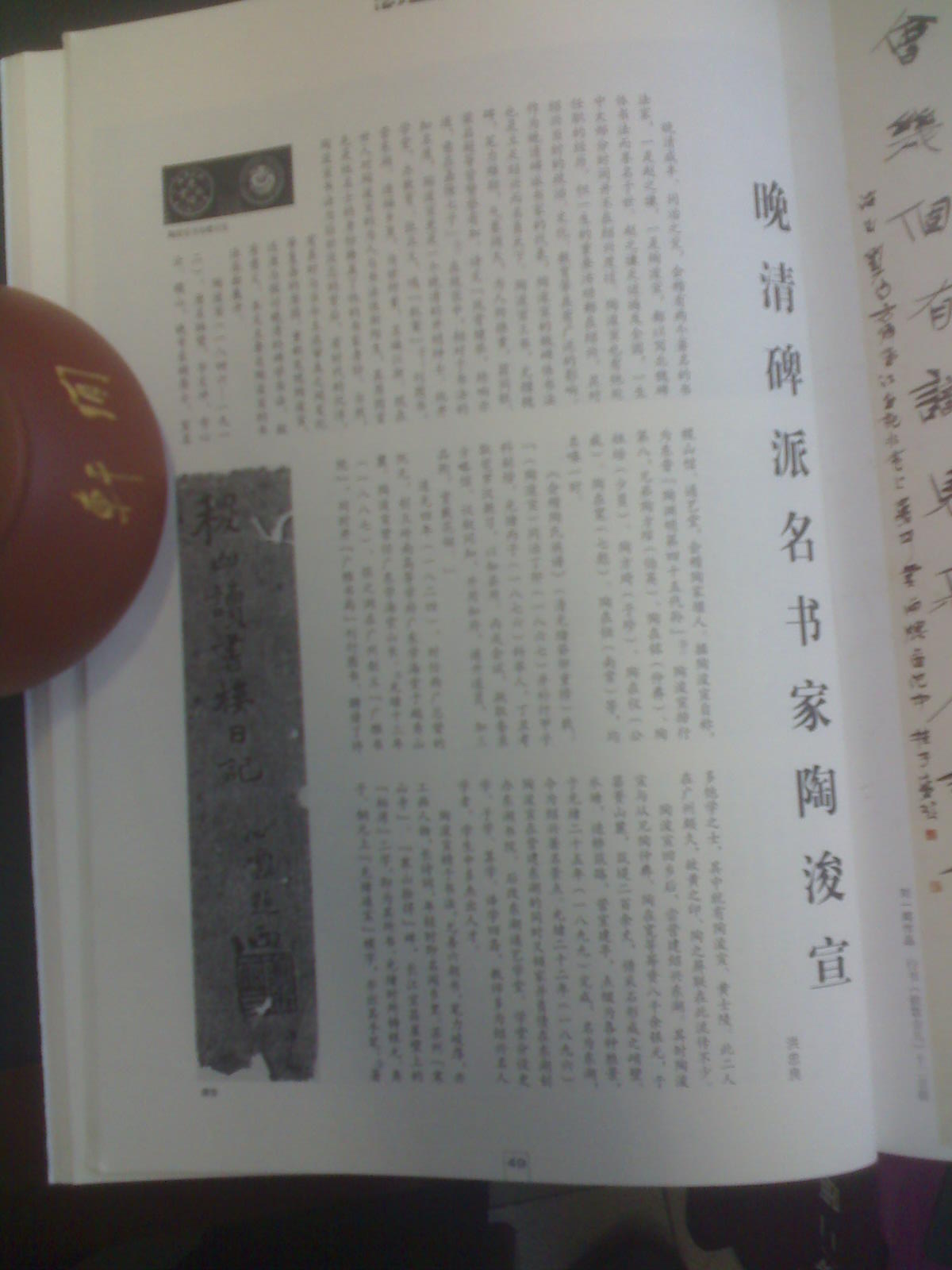
插图版
碑派大旗下的绍兴书家陶濬宣 (订正版)
洪忠良
【内容提要】清嘉、道年间,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包世臣《艺舟双楫》定扬碑抑帖之基调。同、光年间,康有为吸取了清代金石考据学的最新成果,续包世臣为《广艺舟双楫》,集碑学理论大成之作,举世瞩目。在此大背景下,会稽先有赵之谦,后有陶濬宣,两人书法均以碑派面目闻名于世。历来研究赵之谦者众多,研究陶濬宣者希少。本文主要从陶濬宣的生平活动,与陶濬宣同时代翁同和、杨守敬、梁启超、张謇和当代沙孟海等名人的评价,考察流传的墨迹等入手,努力对陶濬宣书法的做一客观评价。
关键词:碑派 书法 陶濬宣
清嘉庆、道光年间,随着古代石刻碑版的大量重新发现,阮元应时而著《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竖起了第一面鲜明的碑派旗帜。他认为正书行草可分为南北两派,又认为北派书家长于碑榜,南派书家长于启牍。一时间,北碑成为弥补帖学糜弱的一剂良药,包世臣、康有为等,更是著书立说,大力鼓吹,为清代碑学的中兴摇旗呐喊。本文所述陶濬宣正是晚清书坛碑派大旗下的代表书家之一。
同治、光绪年间,继赵之谦之后,会稽又出了一个大书法家陶濬宣,也以写北魏碑体书法而享名于世。陶濬宣工书,尤擅魏碑,笔力雄劲,气象阔大,为人所推重。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北魏造像,至今存者盈千累万。中之最佳者,有龙门之《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称为《龙门四品》,后又增为二十品。迩来说北碑者大抵从此入手,遵义莫友芝、会稽陶浚宣其最佳者”。翁同和、梁启超等皆赞誉有加。陶濬宣诗文“风骨健举,结响亦遒,意在嘉隆七子”①。在现实中,相对于书法的知名度,陶濬宣更是一个晚清的开明绅士。他开学堂,办教育;张正义,鸣“秋案”②;刊图书,营东湖。造福乡里,为世所重,名遍江浙。当代世人对陶濬宣的为人与书法逐渐陌生,其原因首先是他名士的身份掩盖了他的书家身份。当然,陶濬宣书法为后世淡忘的背后,有时代的沉浮,有其时与当今主流审美之间变化等复杂的原因。重新发现陶濬宣,还原与探讨晚清的碑派书法,极有意义。本文主要自陶濬宣的书法层面展开。
陶濬宣(1846—1912),原名祖望,字文冲,号心云、稷山,晚号东湖居士,室名稷山馆、通艺堂,会稽陶家堰人。据陶濬宣自称,为东晋“陶渊明第四十五代孙” ③。父陶庆怡,兄弟陶方琯(伯英)、陶在铭(仲彝)、陶祖培(少蒷)、陶方琦(子珍)、陶在仪(公威)、陶在宽(七彪)、陶在恒(南常)等,均名噪一时。陶濬宣排行第八。
《会稽陶氏族谱》(清光绪癸卯重修)载,“(陶濬宣)同治丁卯(1867)并补行甲子科副榜,光绪丙子(1876)科举人,丁丑考取觉罗汉教习,以知县用。丙戌会试,挑取誊录方略馆,议叙同知,升用知府,递升道员,加三品衔,赏戴花翎”。
道光四年(1824) ,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创立岭南高等学府广东学海堂于越秀山麓。陶濬宣曾任广东学海堂山长④(学海堂不设山长称学长)。光绪十三年(1887),张之洞在广州创立“广雅书院”,同时开“广雅书局”刊行图书,聘请了许多饱学之士,其中就有陶濬宣、黄士陵。光绪十七年,曾国荃于潮州金山建书院,延之主讲席。
陶濬宣回乡后,尝营建绍兴东湖。其时陶濬宣与从兄陶仲彝、陶在宽等筹资8000余银元,于箬蒉山麓,筑堤二百余丈,借采石形成之峭壁、水塘,造桥筑路,营室建亭,点缀为各种胜景,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完成,名为东湖,今为绍兴著名景点。光绪二十二年(1896)陶濬宣在营建东湖的同时又倾家并负债在东湖创办东湖书院,后改东湖通艺学堂。学堂分设史学、子学、算学、译学四斋,教师多为绍兴名人学者,学生中多杰出人才。
陶濬宣精于书法,尤善六朝书,笔力峻厚。亦工画人物,长诗词。年轻时即名闻乡里。苏州“寒山寺”、“寒山拾得”碑,即为其所书。光绪时浙江所铸银元“光绪元宝”模字,亦出其手笔。⑤著有《稷庐文集》、《稷山读书札记》、《稷山读书楼日记》、《稷山札记》、《修初堂诗草》、《稷山文存》、《稷山论书诗》、《稷山居士客定海厅幕笺启》、《稷山杂文》、《稷山诗存》、《通艺堂诗录》、《稷庐文集》、《稷山狮弦集》、《国朝绍兴诗录》、《稷山馆辑补书》等。
陶濬宣书法“上自秦汉,下迄六朝,无所不学,每临一碑,辄至数千百遍,临池之勤,自幼至晚年,不缀寒暑。” ⑥“自幼至晚年”从中不难看出陶濬宣于书法的用功与刻苦,“上自秦汉,下迄六朝”是说明了他书法的取法范围,就目前流传的作品来看,这个范围内的书法对他来说确实情有独钟,并作诗九十余首论书法源流。视陶存世稿书而外,其严格意义上的书法作品都明显带有六朝碑版的的痕迹。他在风格的营造上也是有意识的。他的部分摩崖题字,可以看出取法《郑文公碑》与《龙门造像》诸碑的痕迹,简直可以与六朝文字互乱真假。也正是这一类作品,为他赢得了不少名声。其书法知音翁同和“陶心云谈书法,盖包(世臣)派也;然是英雄,不依人”、“善六朝书”⑦的评价不是浪得虚名的。这种石上作品,是否是因为翻刻上石后无法做到笔画光洁而多出了一些斑驳的金石味道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就现在传世的陶濬宣碑体墨迹来看,其大字作品多点画劲挺,并无斑驳的意味。陶濬宣的作品主要就是这些具有浓厚魏碑风格的楷书作品。这些作品结字平阔而宽绰,注重横向的取势,融入了篆隶笔意。从墨迹本上看,这类作品点画劲挺,墨色浓厚。许多人对他书法面貌的印象仅限于此,评论也多以此展开。
清代湘人杨钧(字重子)《草堂之灵•横扫》一文云:“陶濬宣书用廓填法,乃吴跃金之言。又闻其鬻书燕京时,赵之谦疑其书法有异,乃混作古董客,直入其斋。陶正挥笔,未及中止,管端内向,横卧扫之。赵归仿制一联,悬之纸店。一日陶至,细审久之,问曰:‘此联何来?余实未制’店主语其故,陶殊忸然。盖陶之书,廓填与横扫并制也。” ⑧陶濬宣魏碑风格的大字作品,批评者多指责其为求刀刻斧斫的北碑效果,用了怪异、生硬的创作方法,为人所不屑。这些故事的叙述中不乏杂有刻薄的言辞。是否要对陶濬宣此类大字书法全盘否定,予以取笑,当先思考两个问题:首先是这样的作品是否有意义?梁启超当年对陶濬宣很崇拜,并说自己写字是受了陶的影响。梁在《稷山论书诗序》中说:“计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堂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联,目眩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京师识心老,盖在夏穗卿座中,心老即席见赠一帖,文曰:‘学问文章过吾党,东南淮海维扬州。’且曰:粤地在禹贡固扬分也。其书龙跳虎卧,意态横绝。亡命后,帖久烬,然神理深镂吾目,及今犹可仿佛。心老论书,尊碑绌帖,此道、咸以来定谳,不可不知也。”⑨ 梁以为陶濬宣书法“龙跳虎卧,意态横绝”是有其独特而不低的艺术境界的。在今天来看,陶濬宣的创作如真为了某种效果而创用一些常人不用的方法的话,其意义也是积极的。其次,陶濬宣书法的创作真的有所谓的“廓填”与“横扫”吗?廓填法,也叫双勾填墨法,始自六朝人,为移模碑帖之用。杨钧《草堂之灵•记陶》一再说明陶濬宣书法乃用此法:“陶濬宣颇有字名,李梅庵(瑞清)甚为赞许,然其书严整而无生气。余尝疑其书有疑。汉阳吴跃金,与陶交善,云其作书甚秘,不肯示人,纯用廓填法,无一笔为写出者。” ⑩从陶濬宣作品来看,他所描述的“严整而无生气”确实存在,似乎不可能是先双钩后填墨的。杨鈞自吴跃金中得到的是陶濬宣书写是“不肯示人”,又哪来“纯用廓填法”一说呢?显然是其自己妄自揣度,缺乏根据。而前文所说能“横扫”,也证明了陶濬宣独特的用笔方式,那也就不是填墨那么低级了。文人书法往往具有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他们一般注重书写的过程,即使作品的韵味差强人意。作为文人的陶濬宣,也不会沦于这种工匠的技术性工作。南通状元张季直(謇)就明确的指出:“(陶濬宣)写字用卷笔法,不合古法。”⑾ 可见陶濬宣的笔法或应该是卷笔法,而绝不是廓填法,这就有本质的区别了。
其实,陶濬宣的这些魏碑风格的大字作品与赵之谦的魏碑风格的书法取法相近。沙孟海在《近三百年书学》中说:“(赵之谦)把森严方朴的北碑,用婉转流丽的笔致行无所事地写出来,这要算是赵之谦的第一副本领了”“赵之谦有个同乡叫做陶濬宣,他也专写北碑——专写《龙门造像》的——写的太板滞了。我认为与其像陶濬宣这般板滞,不如像赵之谦那样流动,好在他与流动中有钩勒,不至于全没骨子”。⑿即说赵之谦在书写与墨色上处理较为活泼,艺术感就高明了许多(沙孟海在《陆维钊书画集前言》中又讥赵、陶为写北碑末流了)。陶濬宣的早中期作品明显是追求字字稳健,笔笔有力,由此走到了一个极端,才产生如此面目。在陶濬宣部分书法笔画板滞光洁的背后,可能有他用纸的原因。陶氏家族富甲一方,陶濬宣偶用当时流行的蜡笺纸作书,且喜用极浓之墨,此纸光洁不吸水,墨色又不易变化,再加上他独特的用笔方法,点画就显得平实有余,虚灵不足了。笔者所见,陶晚年大字作品就灵动多了。
相对陶濬宣的大字作品,他的小字作品则鲜活许多,面目有正书、行草之分。李慈铭论陶濬宣:“心云教授自给,予与交甚疏,而远道相思,束修分饷,今人所仅见也,词翰高洁,亦有魏晋之风”。⒀李氏论语,不仅说出了陶濬宣人与文的特色,也可以来比喻他小字正书、行草书。因为陶濬宣的小字书法十足一派魏晋之风,行草稿书不逊当时帖学大家。这类作品,或为稿本,或为题跋,或是照相之类的说明文字。随手写来,奇巧活泼,没有大楷作品的规整庄严。从这些小字书法中,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魏晋碑版的笔调,或行或楷或草,轻松而质朴,毫无匠气。这是他“自幼至晚年,不缀寒暑”的笔底流露,无意于佳而自佳者。就单单这些作品,推想当时陶濬宣书法的盛名,确信不是空穴来风,应该说还算是实至名归的。
陶濬宣书法书风质朴,乃习六朝文字之代表书家,一时影响江浙沪。如少年马一浮的作品就深受这种六朝古质书风的影响。今日所见其弱冠所作《自题十八岁影》“结体宽绰而略方扁,笔画有力而棱角分明,可见马一浮早年亦受时风浸染,曾力学六朝碑版。”⒁不难发现,马一浮此作与陶濬宣的小字书法有其极为相似相近的一面,甚至将“结体宽绰而略方扁,笔画有力而棱角分明”的描述用在陶濬宣的小字书法上,也是十分恰当的。
陶濬宣生活在中国晚清旷古未有的大变局年间,其一生言行与艺术实践追随甚至引领了那个时代的节拍。作为传统士绅,承继江南士大夫文化的历史惯性,社会要求他们要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诗书琴画、文物鉴赏等。而在开维新风气之先的广东等地的见闻,进一步影响了他趋新、经世的意识。如果说陶濬宣经营的东湖是古典的江南传统,那么,他魏体书法是趋变的古越天性。而他对书法的审美取向,正反映了一时代对碑学的思考与实践。纵然他当时的影响广泛,不过随着碑学审美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他许多积极的尝试与探求竟然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毛泽东有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碑学“新天”已成,“壮士”功劳在前,我们还是不能忘怀的。
注释
①谭献《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版 第57页
②据陶沛霖《秋瑾烈士》一文回忆,“秋瑾就义后,陶心云驳浙抚和绍兴知府致电军机处,电文很长,谓:‘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电文揭发贵福之暴行很详”。
③《会稽陶氏族谱》,清光绪癸卯重修本。
④蔡元培《致陶濬宣函》在《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版第1页;汪祖泽《广州学海堂》载《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七卷第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⑤浙江造《光绪元宝》,面文中间“光绪元宝”,珠圈上环为“浙江省造”,下环为“库平七钱二分”,币文魏体楷书为陶濬宣写。陶书《光绪元宝》,现价每枚已达15万元人民币。“光绪元宝”字肖新魏体楷书,新魏体源于北魏书体,盛行于清末,几经变化,至今已成为印刷体美术字。写新魏体时,有人将笔锋剪掉,使笔介于毛笔与毛刷之间,以求笔画挺劲、外方内圆、棱角分明。陶濬宣书法为其滥觞。
⑥《绍兴市志》,册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3117页。
⑦陶濬宣到过北京数次,都拜见过翁同和,清翁同和对陶濬宣的书法深为佩服,曾手书相邀,并在信内申明:“免去官礼,彼此轻衣小帽相见。”翁同和在其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初六的日记中载:“陶文冲(濬宣)来见,此君善六朝书,能诗,今在广雅书局”;又在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初七的日记中记:“陶心云谈书法,盖包(世臣)派也;然是英雄,不依人。”见《 翁同和日记》,中华书局,2006版光绪十六、十八年,相关条目。
⑧杨钧《草堂之灵•横扫》,岳麓书社,1985年3月第1版 第310页
⑨梁启超《稷山论书诗•序》载《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六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885。为了继续深造,梁启超以秀才的身份进人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不习八股,所课内容为汉儒的考据学、经史、词章以及宋儒的性理之学。系统学习了有关词章训沽和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识,梁启超对乾嘉汉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⑩杨钧《草堂之灵•论陶》,岳麓书社,1985年3月第1版 第168页
⑾张謇《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⑿沙孟海在《近三百年书学》、《陆维钊书画集前言》载《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第40页、第213页
⒀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⒁方爱龙《中国书法全集•李叔同、马一浮》,荣宝斋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244页
|